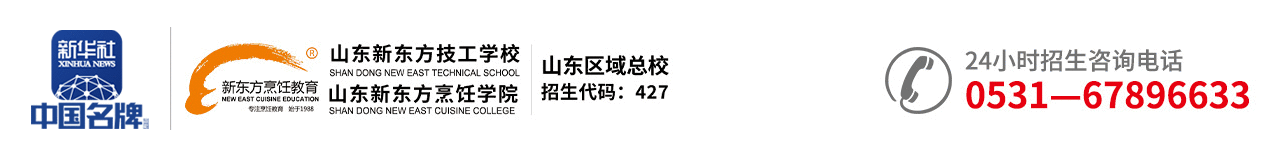吃相是吃喝的行为规范。各国、各色人等,对吃相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欧洲世袭的王公贵族,从来不以娇贵的嘴唇直接喝汤,而是用汤勺舀起汤汁,温文尔雅地送进尊贵的口中。更有甚者,他们不但禁忌喝汤时弄出声响,而且从不由外往里舀汤,认为那是没有教养的吃相;然而,高等洋人抓起烤肉撕咬之后,竟然津津有味地舔吮油腻的手指头,平素道貌傲然的绅士风度即刻荡然无存。东南亚的许多,有关男性吃相的规定却颇为滑稽:不准用左手拿食物吃。理由不言自明,因为女人并无这个禁忌。
吃相规则并非一成不变。电视系列片《 DISCOVERY 》(《发现》)讲: 1837 年,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捉到一个西方传教士,他们将白人当作异类,于是聚而吃之。某个土著人分到一截雪白的臂膀,便顺着小手臂往手掌啃咬,谁知屈死的传教士灵魂尚存,并未僵硬的手指竟然猛地弯曲,抓瞎土著人的眼睛。一件不起眼的小事,往往会改变历史进程。从那以后,食人族对吃人就有了禁忌,几年后就根绝了野蛮吃相,进而彻底放弃原有的拜物教,改为笃信白人的 GOD (上帝)了。这段轶闻看似离奇,却有“信仰事小,吃相事大”的意味。如果土著人固守其祖先吃人的规范,恐怕至今仍然以吃异族人为人生一大快事呢。
吃相难看的要数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,“吃个老母猪不抬头”的自我戏谑中透出黑色幽默。成都人的文化底蕴深厚,我们讲究吃相。如果某人吃饭的仪态不雅,我们就会委婉提醒人家吃喝的姿态要“周吴郑王”(借用《百家姓》的方言,中规中矩之意)。不过,我们有时却毫不顾忌吃相———吃小火锅时,夹起毛肚的两根“篙竿”(筷子)的夹角起码大于 60 度,喝酒更要敞开喉咙大声武气地划拳,豪迈之气倒是直冲霄汉,但在旁人眼里,那吃相却很难可圈可点。
吃相其实是游离不定的饮食语词。在特殊情形下,另类的吃相,有如新新人类用“很中国”、“男人”等莫名其妙的词汇颠覆汉语语法。兔脑壳是成都人老少咸宜的新潮零食———五香、腌卤、麻辣、烟熏……各种味型的兔子脑袋,叫人垂涎不已,巴不得对它们优游地解构一番。品尝兔头固然没有一定之规,先啃咬其下颚或先吮吸其脑髓,悉听食者尊便,但必须注意吃相,切莫张开嘴巴乱啃乱咬一通。媒体曾报道吃兔脑壳大赛的盛况,某女士不仅啃得既多又快,而且以其无比曼妙的吃相博得满堂喝彩,于是理所当然地荣膺冠军。这段逸闻的意义在于,现代成都人完全摈弃了兔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陈腐观念。我们即使看到白领姑娘一边啃着兔头,一边在春熙路闹市区徜徉,也绝不会觉得稀奇;尤其是在姑娘殷红的嘴唇与油亮的兔头相映成趣的当儿,人兔对话的友好界面,顷刻就化作一处处现代版的都市街头流动风景。
卡罗琳·考斯梅尔(美国作家兼美食家)这样定义饮食行为:一种指向某个对象或其他对象的有意识的活动。既然是有意识的吃喝,那么,吃相好坏似乎就是无关宏旨的小问题。我们几乎可以断言,所谓“吃相”,在特定场景下却是吃喝的悖论。在至爱亲朋小聚时,我们不能拒绝精美绝伦的家常川菜,更不想效仿忸怩作态的新好男人,干脆把劳什子吃相丢到爪洼国去了。